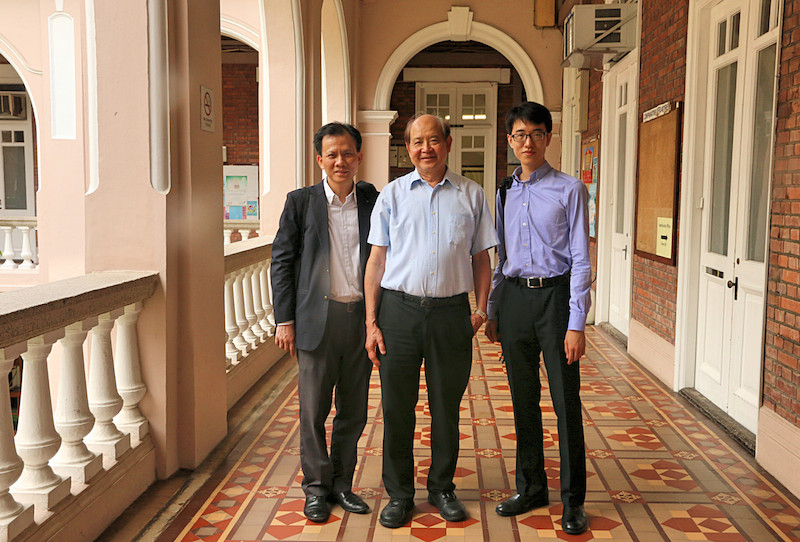Communicate
Alumni Stories
Alumni Stories
【兩代數學人對談下篇】 教育應以學生潛質為本
Professor Siu Yum-tong
蕭蔭堂 BA 1963
(內容來自2015年8月2日灼見名家專訪 )
(前文蕭教授談到,數學教育的重點應在於理解基本概念和培養思維能力,而非操練運算技巧或灌輸專業知識。)
撰文:盧安迪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蕭:蕭蔭堂教授
盧:盧安迪(筆者)
文:灼見名家傳媒社長文灼非先生
盧:香港的中學數學課程側重於代數、幾何等連續數學(continuous mathematics),其中一個原因可能跟職業導向有關,因為連續數學較多在專業中直接應用。但根據你剛才指出的教育哲學,數論、組合等離散數學(discrete mathematics)也同樣能培養思維能力啊!
蕭:但要考慮一個因素,就是大部分人對學術的興趣都不是很大。而且社會也有不同的分工,不需要每個人都做學問。人類歷史上,真正的創見的新發明,從來都只是倚賴很小部分人。
精英創見改變世界
我個人認為精英制度是很重要的。當然,民粹的思想多會反對精英制度,但要培養出那少數有原創性、有影響力的精英,就不能全部人都「一刀切」。而培養這一小部分精英的學府多是私立的,例如哈佛、普林斯頓,因為它們不受民粹的政府控制。雖然英國的牛津、劍橋是公立的,但它們有這麼多年的學術傳統,又有很多私人捐贈,可較獨立自主地運作。香港的大學也有私人捐贈,但主要還是由政府資助和規管,所以不敢,也未必想推動精英制度。
盧:你讀過香港大學,也在美國讀過研究院。你在美國大學任教,也不時回來香港的大學當訪問學人。你覺得美國和香港的大學數學教育有什麼最大分別?
蕭:美國的大學分很多檔次,頂級大學跟社區大學相差很遠。雖然香港也有分學士和副學士,但檔次沒有那麼明顯。香港的教育是以制度為本位,不能輕易改變。美國的教育則以學生的潛質為本位,不太拘泥於制度。當然,香港注重制度的好處是較容易管理。但美國則可以有一些頂級的中學,教很進階的課程,還有不少夏令營等課外學習機會。香港也有很多興趣營,但學術深度則遠遠不如。
盧:是啊,而且美國的高中是學分制,可較自由選課。你剛才提到的頂級高中,例如 Phillips Academy Andover 等,他們一些課程已達普通大學二、三年級的程度。香港則是全部人都讀同一課程。
自由選課發揮潛質
蕭:是啊,美國真的是讓每個學生的潛質盡量發揮。香港要這樣做則很麻煩,因為有一個統一課程,除非把一些特別優秀的學校劃分出來,特別安排。就像從前中國大陸也有少年班,特別培養尖子,香港反而沒有這類機制。美國則不需要少年班,因為全部美國學校本來就是自由選課。
蕭:香港學生習慣循規蹈矩地讀書,最多課外多學一點,但氛圍有限,如果去美國會覺得有很大差異。美國學生較喜歡跟教授討論前沿的研究,香港則較少這種機會。
盧:你覺得香港學生對數學的興趣,跟美國學生怎麼比?
蕭:很多時候,興趣是與生俱來的。我從前在耶魯大學任教時,有一名同事叫 Serge Lang。(盧:噢,他很有名!)他在大學最初是讀哲學的,後來才轉讀數學。我問他為什麼,他說一個人的智力發展跟生理階段是有很大分別的。讀大學前的人生,大部分都是父母、家庭安排好的。18、19歲這段所謂 sophomoric(不老練、一知半解)的時期,開始自立,又初嘗男女關係,甚至想像將來生兒、弄孫,喜歡思考人生。Lang 說如果18、19歲不喜歡思考哲學,就是不正常了。這段時間的思考,可能有結論,找到人生方向,也可能沒有結論。但無論有沒有結論,Lang 說過了19歲就必須停止沉迷思考人生,否則就是不成熟了!
同儕交流勝於競爭
談到興趣,社會的力量和同儕的壓力(peer pressure)是很關鍵的。如果沒有同道中人,你會想:「哎呀,我是不是很怪呢?」相反,我在普林斯頓讀研究院時,沒有必修的核心課程,我和幾個同學便一起看書摸索,然後開一些非正式的研討會互相講解,大部分知識都是這樣學回來的。香港就是缺乏這樣的環境,不知是否因為競爭性太強,怕跟同學交流後,旁邊的同學會超越自己。
盧:在香港,做學問常被視為非主流的出路。很多人的觀念是,讀書好就應該做醫生、律師。
蕭:醫生、律師有牌照制度控制數量,不容易失業,較有穩定性和安全感。金融業能賺很多錢,所以這些工作在世界各地都是很吃香的。但為何美國比香港有更多年輕人樂意投身科研?首先是因為中國人社會的家庭因素很重要,家長的期望對子女的事業選擇有很大影響,還有一些家長想在親戚面前炫耀自家的子女做了醫生、律師等等。你可能也有這些壓力吧?
盧:哈哈,我的父母從來沒有要求我讀什麼,反而有很多其他同學的父母問我為何不讀醫或法律,所以我覺得很多香港人的心態都是這樣的。
量化壓力不利學術
蕭:美國、歐洲等西方社會,家庭的影響就相對小一點。此外,1960年代,蘇聯剛發射了衛星,美國於是大力投入科學發展,讀科學的畢業生不怕找不到工作。沒有了生計的顧慮,他們便可自由選擇自己喜歡的專業。但這個因素在越戰結束後已小了很多了。
文:你多去內地講學嗎?
蕭:有,而我發覺最有效的講學方式,是講學問背後的基本原理。
現在學術界的評估指標十分量化,例如看發表論文的數目、期刊的影響因子(impact factor)等等,對學者造成很大壓力。從前較多終身制的教職,目的是讓學者專心做研究,不受外界影響,例如人文學者不受政府或社會輿論壓力影響,自然科學的學者也敢於做一些較困難,要花較長時間才出成果的題目。(盧:例如 Andrew Wiles 閉關7年以證明費馬大定理!)所以現在學術界的競爭大,討論少,雖然很多研討會,但當中的學術報告多為「廣告」性質,而非深入交流,唯恐自己的構想被同行取用,捷足先登。
所以我希望多講解課題的歷史背景、基本構想、將來可能的研究方向等等,跟同行深入交流,推動學問發展。
蕭蔭堂教授簡介
美籍華裔數學家,哈佛大學講座教授,原哈佛大學數學系主任。研究領域包括分析、復幾何、代數幾何、微分幾何等。出生於廣州,1949至1960年分別在澳門和香港培正中學就讀,1963年獲香港大學學士。後赴美國留學,1964年獲明尼蘇達大學碩士,1966年獲普林斯頓大學博士。畢業後曾任教普渡大學、聖母大學。1970年起先後任教於耶魯大學、史丹福大學、哈佛大學。哥廷根科學院通訊院士、美國文理科學院院士、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、中國科學院外籍院士、中央研究院院士。
我發覺最有效的講學方式,是講學問背後的基本原理。